
金馬九項入圍大熱門《五月雪》上映後,該片導演張吉安曾經談論本片是「只能在異鄉溫柔的讀的給家鄉的情書」,這部穿越時空,從1969到2019的兩段式電影,展現了馬來西亞不能談論的禁忌話題:
一場至今弄不清死者身分的大屠殺。
侯孝賢與阿比查邦風格?
其實拿侯孝賢或者阿比查邦來看張吉安最初是一種常見的宣傳策略,因為一個新導演我們往往習慣用名導的來描述以增進觀眾的興趣,尤其如果導演自己有表達對特定導演的偏好,那麼我們就更容易順著導演的指出的某種偶像來描述該導演的「優點」比如說有些人在張吉安的電影裡看到了侯孝賢的長鏡頭或是對遠景的著迷,還有這種對「童年往事」的留念,畢竟《南巫》他就直說這是改編自己父親的故事,其父自從被下降頭後就成了乩童,而張吉安其童年更有目睹過許多怪奇的往事,這就是為什麼其提到阿比查邦,在阿比查邦的世界裡,這些事情也很正常。
但這種語言描述策略一個很大問題就是,如果導演真的脫離了他的偶像的影響,而越來越在其新作品裡展現他自己,那麼他以前那些被稱讚為像某些導演的優點就會馬上變成一種拘束,一個很簡單的原因是,張吉安年過中年才當導演,然而其除了本科是念電影之外,還是一個多年的廣播人還有戲曲人甚至是人類文化田野調查人,這跟侯孝賢野路子出身直奔片場或者阿比查邦裝置錄像到藝術電影的路徑有天壤之別,更多的帶有某種知識分子的色彩,這就是為什麼要論解釋自己的作品的能力,張吉安會比這兩位前輩還厲害,因為他是先深度的了解這些他拍攝的事物背後的強烈的因果關係,而非以一種神話式的或者是氛圍取向的策略來經營他的電影,你在他的作品裡面找不到什麼知識上辨認不出來的東西或者難以解釋的選擇。
更詳細的說就是,張吉安的電影,是在試圖去理解他過去所經歷的一切,乃至於那些超自然但仍然具有真實生活質感的事情,他在疏理這些事情的過程裡,發現了種族、文化、宗教等多樣元素的介入還有一個繁複的權力場域,而他所做的就是將其再現出來甚至是除魅化的,而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呈現超自然事物,比如說白皮膚的小鬼,或者是被困山洞的珂娘時,一切都如此清晰且可見,彷彿人神之間的界線就像各種種族、文化、宗教等多項差異那樣是可以跨過的,其中沒有任何「跨不過去」的事物。
就像他父親告訴他的,他並沒有當乩童的天份。
張吉安清楚的知道這一點,以致於當他在自己的電影,無論是《南巫》或者是《五月雪》時,比起「他扮演的對象被再現」這件事,更重要的是去「再現對象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他真正強調的,不是這些具有差異性的馬來西亞多元文化,者神怪傳說,從他這個馬來西亞華人看來有多獵奇多刺激,而是他們處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網之內。
然而到了《五月雪》,《南巫》的「懸念」則成了一種「留白」,這裡有了「跨不過去」的事物。
「從小我在外面玩太晚回家時,婆婆就會恐嚇我,你再不聽話,『513』就把你吃掉!當時我以為那是一個怪物還是什麼。」
513首先以怪物的身分進入張吉安的生活,而他至今所做的一切都在試圖理解它。
《南巫》到《五月雪》的性別延續與策略轉向
在《南巫》裡面,延宕在整個故事的事件首先是一名女性阿燕的丈夫阿昌莫名生了怪病,甚至會吐出鐵釘,就醫無果下,不信神的她只好尋求馬來西亞上各種宗教與儀式,來試圖拯救丈夫,那是華人祭拜版的拿督公,是歸化為伊斯蘭解降師的暹邏師父,也是山洞裡的珂娘,珂娘從中國而來,被馬來巫師愛上,強硬施法使其留在這裡,並最終接受當地服飾紗籠,有別於外界謠傳其脾氣不好,她幫助了同樣身為女性的女主角。
在這過程裡觀眾也會對宗教與儀式產生思考,在馬來西亞這個多元之地,你根本不知道你惹到什麼超自然力量,而這些超自然力量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比如當珂娘要阿燕把其丈夫阿昌平日喜愛祭拜的拿督公與其衣物沈入大海時,我們便看到了某種女性超自然力量,對男性超自然力量的反擊,拿督公的乩身講話暴躁且憤怒,而珂娘溫柔且平靜,阿燕則聽從其指示,來到丈夫被下降頭的大樹下,拿起馬來西亞的儀式劍大喊:「我不怕你了!」儼然已從這一切混沌裡站穩腳跟,不只是對降頭鬼或者背後下咒者,還是對這一切反覆跌宕的生活,包括體現權力競逐的語言政策,我們不能忘記在電影設定的1987年,去年入獄的馬來西亞首相納吉也曾在惡名昭彰的「茅草行動」說道,他不會收回馬來短劍,直到上面沾滿華人的血。
其實如果真的要替張吉安這樣的奇幻恐怖電影尋找一種近親來比附的話,更像是威廉·佛雷金知名的恐怖經典《大法師》,因為本片同樣也是一名不信教的女性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才慢慢從相信科學逐步皈依天主教信仰,所以擺在她面前的是「信與不信」的問題,而在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多元種族、文化、宗教的相互衝突與相互影響體現在本片裡,你完全無法只依靠一種力量在此求生存,伊斯蘭文化在馬來西亞的主流化一方面成為穩定馬來西亞政治的基底,另一方面其對其他文化在本質上的排擠也妨礙了馬來西亞的共存與團結。
這就是為什麼張吉安需要拍《五月雪》,在這部片裡,他試圖更加逼近一切的起源,無論是馬來西亞,還是一切的種族、文化、宗教的衝突。
今年《五月雪》是轉向,也是一種回歸,因為早在2018年的《義山》這部短片裡,張吉安就以女性為主角,展現中國戲曲與義山亂葬崗之間的並置,而時序上,《南巫》發生在1987年,該年政府大規模逮捕異議人士並施加酷刑以噤聲人民的「茅草行動」實際上是1969年的「513大屠殺」的延續。
但是513又從何而來呢?
張吉安進一步的追問時,他找到的是狼牙皇帝,還有狼牙皇帝這部電影的編劇,東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他又是誰?
他是馬來西亞開國元勳,而他父親是吉打蘇丹國王
在《五月雪》裡,乍看只涉及了兩個時空,但實際上你會發現,馬來西亞一切都在片中出現的文本裡,不斷的溯源,如同片頭所放置的馬來紀年裡面寫道,控制麻六甲港口的明朝皇帝因為要讓麻六甲王朝的蘇丹臣服,而生了痲瘋病,最終只能藉由喝蘇丹的洗腳水來道歉才能獲得治癒。
換言之,馬來人,曾經拒絕中國的統治而不願屈居於他們之下,然而馬來人掌控的政權在未來的某天成了當年他們反抗的壓迫者,因意外飲血而成為嗜血的狼牙皇帝,這是張吉安置於片中的批判。
至此可見,張吉安的《五月雪》與思想不只是為了華人受害者的權益,還是以馬來西亞為主體性在生長的,否則他只需關注與展示華人離散史的部份即可。
但是不知道上面這些就不能看《五月雪》嗎?
從女性入門的共情不需科普
可能是吃了上次《南巫》票房慘澹的虧,電影裡,《五月雪》這次在字幕上不只寫出許多細小聲響是什麼,還幫一無所知的觀眾科普裡面的各種物件或者標語,可以說非常貼心。
而這也體現了馬來西亞是一個種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之地,這些多元造成了觀眾在知識上接受的隔閡,甚至因此而不敢接近這部電影。
然而我認為本片有很多你不需要先去科普,不需要先查資料也能看懂的東西,甚至我認為這些東西,甚至是張吉安在電影裡做的最好的東西,是這些東西讓觀眾看完《五月雪》之後被為之吸引而跟著去查詢片中的歷史脈絡,自行拼湊這一切來龍去脈的隱含細節。
我們不能夠把《五月雪》看做是張吉安這一生的文史報告,更不是一篇影像論文。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感受的是片中角色的處境,比如萬芳飾演的阿英,她作為一個女性從小就和身為娘惹族的母親受到爸爸的打壓與邊緣化,只因娘惹意味著沾染了馬來文化的不純華人,當哥哥被爸爸帶去給拿督公祝福時,在教室被其他學生霸凌的她,在被母親牽去給父親後,不只沒有受到安慰,母親給父親的,她那被同學弄髒的衣物還被父親嫌棄而不拿給拿督公祝福,即便母親提著飯菜過來。
而當父親帶著她的兄弟去大華戲院(Majestic Theatre)看《負心的人》時,她只能夠被留下來跟母親一起看戲。
多年以後,失去了父親與兄弟的阿英,決定踏上旅程尋找父兄的屍骨,這時電影已經演了超過一半,觀眾也與她一起透過不同的鏡頭語言,來到2018年的當代,外頭世界好像已經擺脫歷史,然而其中仍有事物在騷動。
張吉安在處理《五月雪》時,透過片中權力最低下的女性來做為倖存者,讓觀眾體會到她們的艱難處境與深沈哀傷,阿英與其母親在513中活下來,而母親餘生都在尋求其父親還有兄弟的屍骨,這就是為什麼時空一跳後,作為成年女人的阿英被憤怒的丈夫灑金紙並咒罵她就跟她的神經病母親一樣找墳找到死好了。
在此,一個本該和樂的家庭卻被切成兩部分,只因為一方缺乏了另一方的記憶,他們不像觀眾,與阿英一起感受過那一晚「跨不過去」的恐懼,那是突如其來的槍響與悲鳴,是視域之外的死亡與暴力,她與母親,還有那些同樣失去家人的戲班子們,在戲臺後感受那隔一層廉幕的大屠殺,如同世界各地的觀眾坐在電影院,隔著銀幕,不斷接近,並思考著這一個異樣的時空,那種出自於人,卻超乎於人,不斷揮之不去的恐怖還有傷痕,絕對不只馬來西亞的513事件,而目睹者自此無法與未目睹者生活在同一個位面上。
正如阿英的丈夫先是用柵欄把家圍起來,又在抓到阿英偷偷搭他妹妹的車要前往義山雙溪毛糯亂葬崗時,一邊咒罵一邊拿菜扔她們一樣,性別在此用來作國族分裂的隱喻,一個家因為這樣不再和諧,但這種和諧並非難以解決,只要其中一方不要用自己的「看不見」否定另一方的「看的見」即可,這種「看不見」與「看的見」的差異,進一步呈現在阿英終於抵達的墳場那裏,她不知道她的家人是否真的在這裡,這就是為什麼她的第一站還是得去大華戲院祭拜父兄,因為她知道他們死在那裡,同時觀眾也藉由張吉安的電影看到那台載走滿山屍體且一路滴血成溪的卡車,進一步暗示還沒徹底死去的弟弟在車上的最後煎熬。
而阿英,最終遇見了穿著戲服的女鬼,這是片中另一個與阿英家有關係的家庭的母親,她也在513中失去了自己的母親甚至是她自己的生命,這就是為什麼隔這麼多年她還穿著戲服。
在張吉安的電影裡,女性地位的平等與種族乃至於文化甚至是宗教的平等是同樣重要的,對張吉安而言,過去無法藉由遺忘而克服,這條路終究是走不通的,而如果最被打壓者都能支撐下去持續前行,何以政府要用各種理由推托追尋並展現真相的「團結責任」?
《五月雪》確實不是控訴,而如其所言是情書
這封情書說的是
「是時候帶起那些被遺留在過去的孤魂野鬼,還他們真實容貌,一起走向未來。」
義山的亂葬崗不該繼續是亂葬崗,政府應該公開相關檔案,協助家屬一起還原真相,並讓他們找到家人,以利馬來西亞真正的團結,這就是馬來西亞人張吉安而不只是華人張吉安透過本片想說的,他在本片展現了馬來西亞不被看見的過去,然而這卻不該是終點,因為終點必須由整個國家上下一起努力才有可能實現,這就是張吉安寄寓影像的情感,即便馬來西亞不是刪減就是拒絕他這些關於馬來西亞的作品在本地上映,他也要將這超越時空的情書在世界讀出來,為了走不出來的馬來西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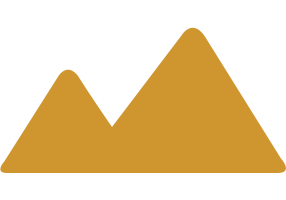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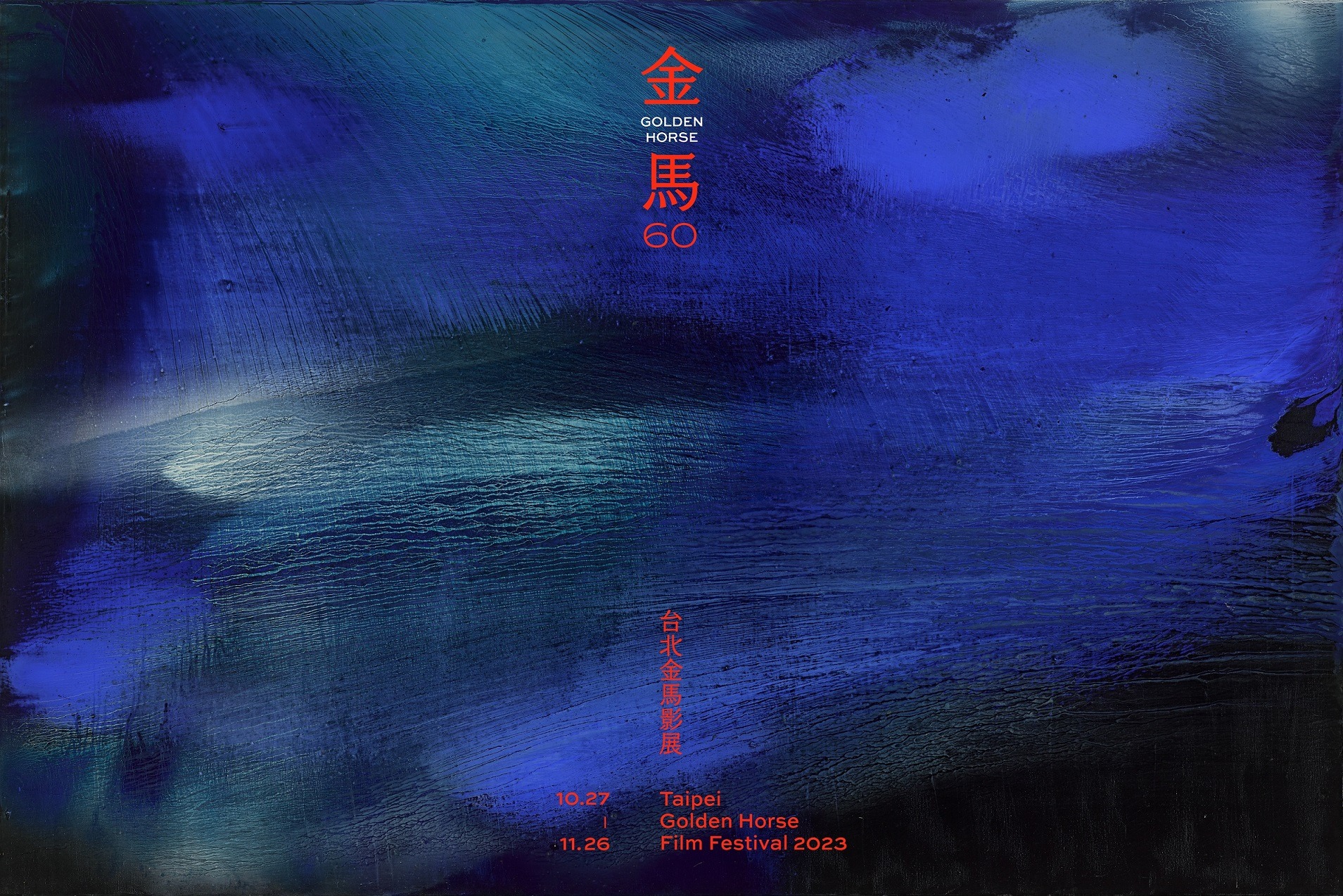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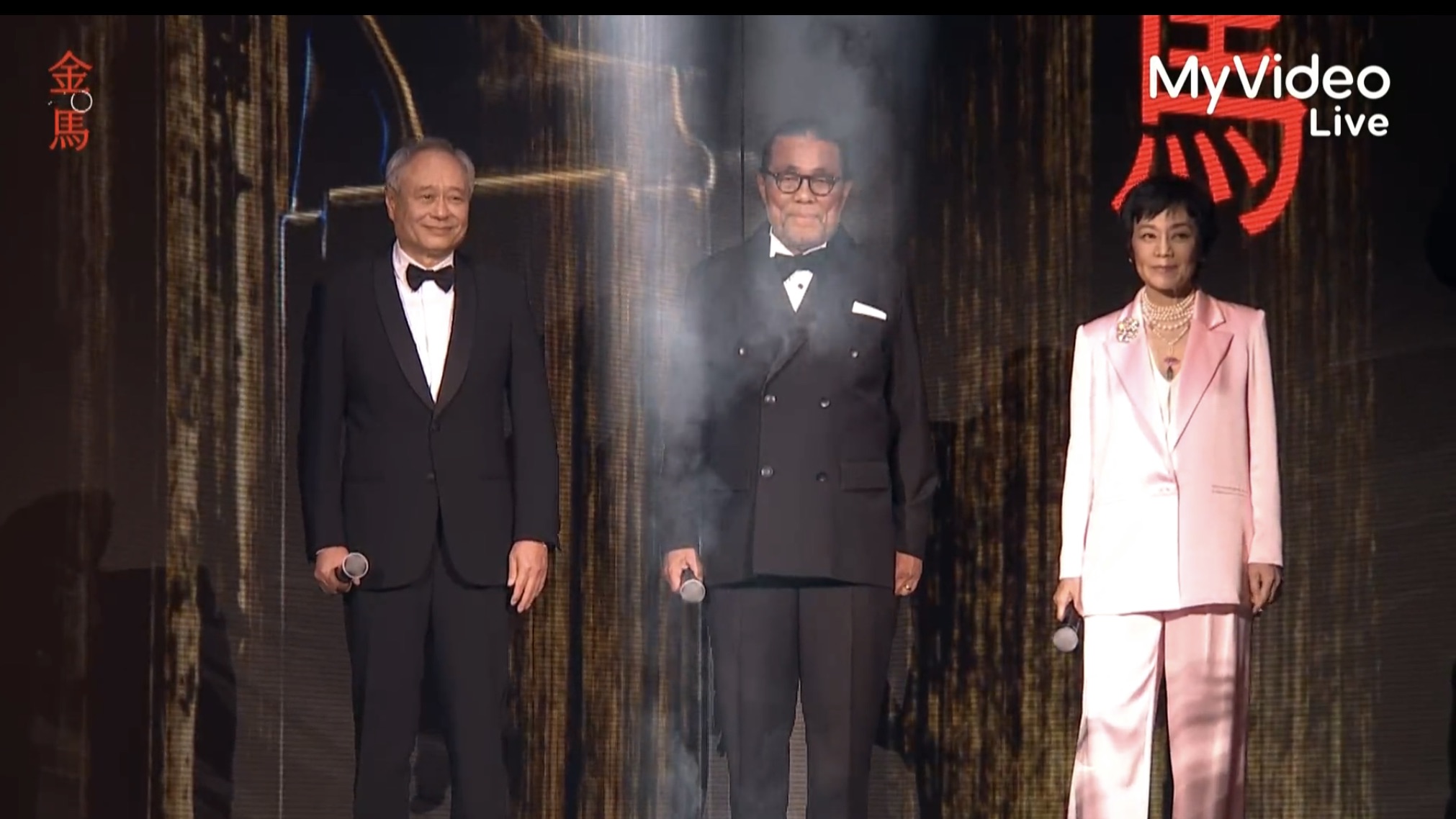
COMMENT